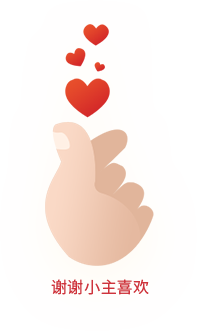逃離當代流水線,殺馬特又殺回來了?
文 | 奇偶派
“葬愛家族集結令,殺馬特派對尬舞之夜,╬∞溡隔倆個仴_/~,液貓倶濼蔀,摋骉特傢蔟,↘侢佽楿藂ヽoo,致那些姩逝去菂啨惷←熟悉的火星文,是不是你當年的qq簽名,讓我們重啟青春的記憶。”
今年7月份左右,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熱愛搖滾的朋友轉發了一條花花綠綠、寫滿火星文,視頻和動圖都頗有復古非主流氣息的線下派對推文。
“8月27日23:00夜貓俱樂部,誠邀各位家族元老GGMM,一起回到精彩耀眼的殺馬特年代。”
一直以來喜歡觀賞土味視頻的我,看到這么接地氣的線下派對邀約,頓時熱血澎湃。
2021年了,曾經消失的鄉村非主流殺馬特,已經復興成了這么城市小眾的娛樂方式了嗎?
殺馬特復興了?
曾經消失的非主流殺馬特,又重新出現在了城市的夜晚派對中。
戴著五顏六色、孔雀一樣的假發頭套、身著花花綠綠的奇裝異服,每個周末,這些打扮“怪異”的男男女女都會聚集到成都市成華區杉板橋中路的夜貓俱樂部,這里有“非主流王族派對”舉行。
“請你不要再迷戀哥,哥只是一個傳說……”,一首曾經紅遍大江南北的網絡歌曲,在夜晚的俱樂部中奏響,現場的氣氛瞬間被點燃,跟隨著頭頂打下來的變色燈光,臺上的男男女女跟著DJ舞動身體,晃動著五彩假發,臺下站立著的男男女女同樣頭戴假發,盡情地跳動起來。
“嗨”是非主流派對永遠的主題,這里是城市打工人工作一周之后,盡情釋放疲憊的樂園。
和朋友一起參加了一次殺馬特派對之后,刺猬被這里深深地吸引住了。今年8月份,夜貓俱樂部開始推出“非主流”主題派對,刺猬漸漸成了常客,“后來,我吆喝了一些想要獵奇的朋友一起去。當時我們玩到了凌晨兩點,結束散場。可以說現在經常出來的朋友都是在夜貓相識的,大家都以家人相稱了!”
這樣的聚會一般有著裝要求,頭戴假發是一般要求,能化妝當然更好。參加一場這樣的派對,正常票價是60元左右,“但如果穿戴整齊、精心打扮,1元也能入場。”刺猬自豪地告訴我,她每場都會化妝和戴頭發,“我可以說是夜貓最尊重dresscode的人!”
經常去夜貓主題派對,刺猬已經對派對流程熟記于心。“當大家驗票進行得差不多了之后,MC會開始放歌,然后會介紹一下自己和夜貓的玩法。”
對于非主流派對,刺猬說,每場非主流她感覺都有一些不一樣的流程,比如有一次有紅毯秀,大家奇裝異服的上去走紅毯,還蠻有意思的。中間也會有一些小游戲,比如酒王爭霸之類的。每放到一首歌,能唱的話也可以上臺去“奪過”MC的話筒,放肆的喊兩嗓子。結束前大概一小時,會有個點歌環節,可以點想要聽的歌,或者就把這個專業的live-house當做你的KTV,上去做個主唱。
因此,殺馬特派對每一場的氛圍都有所不同。
但刺猬每場都盡興而歸,不畏懼任何陌生感,“我每次去都像是得了那個‘社交牛逼癥’,連我朋友都說我像是去夜貓跑商演的打工仔一樣,在臺下就是氣氛組,時不時還上臺唱上兩句。真的是去發瘋的,每次去都累的半死,但是很開心,大家誰也不認識誰,但都很捧場也很和善。所以你想干嘛都可以。”
另一位經常參加殺馬特派對的魷魚說,參加殺馬特派對沒那么多理由,就是“好玩,快樂。”
章魚是成都夜貓俱樂部負責人,她告訴我,夜貓俱樂部是mao的一個新項目,但它不是演出,也不是夜店酒吧,夜貓實行門票制度,而且各個地方夜貓都有不同的特色,成都夜貓俱樂部更注重人情味,目前更偏向互動性,這個特點在后來幫助成都夜貓度過了疫情難關。
其實夜貓在成都2019年就已經有了,2020年疫情突襲,慢慢就有點慘淡了,“我今年三月份接手的,最開始一場夜貓俱樂部能來6個人,最少的一次來2個人。”
壓力下,章魚和小伙伴還是一步步堅持做了起來,其中,人情味主題的派對幫了很大的忙。“目前最有人情味的派對就是殺馬特、夜貓emo夜還有搖滾專場。”她如實說道。
剛開始每場快結束的時候,章魚就在門口拽兩個觀眾問覺得哪里不好玩,哪里好玩,然后交個朋友。就這樣靠著人情味日積月累,一點點磨出來了。“很多顧客都是來到夜貓后交到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看演出看音樂節,晚上在公園野餐。真的我看見他們發的朋友圈都覺得好浪漫。”
最近,老顧客來得越來越頻繁了,很多家人幾乎場場都能見到,現在成都一場能到小200人,但還是很難賺錢,內卷太嚴重。“59塊單人預售票,還涵蓋四款啤酒+兩款飲料酒水暢飲。其他城市夜貓基本都漲價了,只有我們沒漲,成都的娛樂場所太多了,去這些地方玩一圈不點酒水的話,一晚上一分錢不用花。”
說著說著,章魚不由感嘆,“在成都,太難了。”
但這真的是一件讓人開心又有成就感的事,“最初我接手成都夜貓俱樂部就是為了讓來這里玩的人都可以開心,把這里當成一個解壓釋放心事的家。”
逃離當代“流水線”
“好玩、快樂”,同樣也是刺猬喜歡上殺馬特派對的理由,但對于刺猬來說,這份來快樂并不是來得那么容易。
大學學攝影,已經畢業工作4年有余,刺猬今年馬上24歲了,現在做的是朝九晚五、周末雙休的行政工作,但在這份工作之前,也是刺猬剛畢業那會兒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買手店的視覺總監,一份“正兒八經的對口工作”。
當初從銷售崗入職,隨著公司發展和大學專業高度契合,以及老板對刺猬的審美高度認可,短短三個月時間,刺猬就轉職做了視覺工作,開始負責拍攝和設計工作。
后來因為公司人員變動較大,刺猬又擔起店長職責,每日除本職工作外,還要管理店內大大小小的其他事物。一年后老板對她賞識有加,刺猬當上了老板的助理,陪著四處奔波、出差談工作。
這份工作飛速的晉升,刺猬不斷地接受著新的挑戰。“我本就是個有些盡善盡美的完美主義者,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中,我把自己累垮了。”刺猬自詡是個樂觀豁達的樂天派,可讓人沒想到的是,竟會因為自己給自己的心理壓力過大,導致“焦慮癥”這個纏人的病找上門來。
“我病了,病的很嚴重,我自己整日擔驚受怕,也嚇壞了我的家人。”刺猬乖乖看精神科,吃藥、接受了心理治療,并且為了好好養病調養生息,她鄭重地向老板提交了辭呈,老板不愿放她離開,允了她一個月的帶薪假去轉變心情。“可是身體垮了不是這30余日就可以扭轉的,我不知道我和這纏人的心病糾纏了多久。”
后來在家玩了一年半,刺猬被媽媽塞到現在的公司,做了個閑職。每天按時起床上班,在辦公室摸魚。后來又因為一點有的沒的,刺猬接觸到了塔羅牌,才發現,做個神婆好像比之前規劃的種種職業都更要適合自己。于是,她開始做一個早上坐班當行政,晚上回家擺卦算牌的塔羅師。
圖/刺猬的塔羅牌
參加殺馬特派對的年輕人,一般都20出頭,他們熱愛這座不那么大,但好吃好玩的城市。麗莉就是這樣一個典型,2017年畢業,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她決定南下。2018年,她離開從小生活長大的北京,來到成都。
還沒來成都那會兒,麗莉在北京的工作就像是打仗一樣,兵荒馬亂。
當時在一家美術館做引導員,一天值班,早上沒化妝出門,結果就被通知公司大老板去店里視察,然后她只能著急忙慌在出租車上化了個妝,但偏偏司機開車選擇了一條最堵的路線,最后遲到了半個小時,到公司竟發現沒帶鑰匙,又給開鎖公司打電話來開鎖換鎖。
“一天花的錢都快頂上一個星期的工資了,不過還好當時老板沒有要開除我的跡象,本來已經做好找工作的準備了,也算是萬幸。”
北京太大了,“跑來成都,不過是不想家在北京,卻活得像個北漂,出門在外,會讓自己有好像我也是有家可以回的錯覺,心里會有個依靠。”她覺得就像那個被北京開除的人。
“我喜歡成都”,平時周末,除了參加一些這樣的派對,麗莉喜歡騎車逛公園,“成都公園修的都很適合遛彎。”
偶然和朋友一起參加殺馬特聚會,也算是一種緣分。其實麗莉并不怎么喜歡殺馬特派對上播放的那些歌曲,所以一般她都不化妝戴假發。
殺馬特派對吸引麗莉的不是什么殺馬特非主流文化,而是一種一群朋友在一起的氛圍。“夜貓還有非主流殺馬特之外的其他主題,去哪個都是去,而且大家剛好都參加非主流群,所以非主流就像團建活動,一起玩的還是都認識的,就等于是,你和朋友一起去了,到現場又會認識很多新朋友,然后就會越來越多。”
在麗莉所說的殺馬特非主流群中,我觀察到,每天大家都會提到的詞就是“工作、摸魚”。麗莉也是如此,雖然她的工作挺好的,但她就是單純不想上班,“只要是去上班,就是啥也不想干我也煩,工作收走了我的快樂。”
他們說,殺馬特從未消失
為什么曾被嘲諷為“土朋克、山寨視覺系、神經病”的殺馬特,在今天卻能帶給城市青年快樂?
在很多人看來,非主流鼎盛時期的殺馬特是一群來自鄉村、城鎮的低學歷青年,他們憑借著夸張的“洗剪吹”造型嘩眾取寵,高調出現在媒體、網絡、公共場所中,久而久之,這群人便惹人厭惡,被人稱為城市的“怪物”和嘲諷的對象。
2012年,藝術家、紀錄片導演李一凡注意到了殺馬特這一群體,看著他們五彩繽紛的頭發,李一凡激動道,“中國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有人開始特別主動地去抵抗消費主義的景觀,我覺得這是審美自覺,了不起。”
但經過了幾年的拍攝記錄,李一凡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并最終呈現的紀錄片中,呈現了一個和主流媒體報道中截然相反、不為人知的殺馬特群體形象。
這是一群體由留守兒童、十幾歲輟學進廠打工的農民工組成的殺馬特群體。在影片中,這些單純的孩子離開家鄉的熟人社會,來到陌生的工業化城市,很容易被騙和受欺負,為了獲得安全感和吸引人注意,他們頂著一頭夸張的彩色孔雀頭,制造出一種張揚、自信、兇狠的形象,并試圖借此打破枯燥重復、漫長無休止的流水線工作狀態。
后來,殺馬特群體越變越大,他們在通過網絡、線下聚會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家族體系。那時的殺馬特很看重自己的頭發,即便工廠拒絕這樣的夸張造型,很多殺馬特甚至寧愿挨餓,也可以不進工廠。那時的殺馬特對發型特別講究,他們對發根、發尾、角度這些細節扣得特別厲害,當時的發廊老板都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再高的工資、待遇,你讓我把頭發剪了,不可能的”,頭發是他們的信仰,所以當時的殺馬特絕不是假發,都是真當真槍的燙染。
殺馬特對頭發夸張這種形式感其實是出于一種熱愛,殺馬特群體就是一個樂園,所以后來很多人說殺馬特是一種自嘲,李一凡說,其實不是,自嘲不是殺馬特。
在紀錄片中,一位已經讓頭發變回普通人模樣的女生在鏡頭前說,“我以后結婚一定要辦一場殺馬特婚禮。”
很快,殺馬特的記憶停留在了2013年,很多假冒的殺馬特出現,不久便被作為“異端”被封禁,同時,殺馬特群體對自己開始否定,于是,整個殺馬特群體迅速消失在大眾視野。有的殺馬特返回工廠,有的回鄉謀生。
現在,我們仍然能看到一些零星的殺馬特在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直播,但他們的關注度早已大不如前。
城市派對的殺馬特,即使是戴著假發,只在周末晚上出現的城市青年中,依然能看到以往非主流時期殺馬特影子,他們都有在一個群體中尋找快樂和朋友,殺馬特派對是他們在996、疲倦工作之后釋放的樂園。
在這個相同點之外,近年來,中國已經形成一種獨特的工人階級文化,殺馬特時尚只是其中最扎眼的一個例子。當下,一些新的呈現方式已然出現,比如名噪一時的三和大神、隱居鶴崗的年輕人、脫口秀青年等等。
在《殺馬特我愛你》紀錄片中的最后一幕,鏡頭繞著四面都是工人住處的高樓一直旋轉,直到音樂奏響,“像南方夏天一樣漫長,從早到晚,流水線好瘋狂……”
也許,殺馬特從未消失。
寫在最后
為什么殺馬特派對能具有人情味?
也許就是因為它能帶給家人們快樂和歸屬感,即使他們頂著張揚的假彩發,也可以在夜晚派對中忘掉了白日的煩惱。這是他們的共通點。
李一凡的《殺馬特我愛你》為殺馬特正名,揭示了真正的殺馬特是什么。影片中,被稱為殺馬特教父的羅福興說,“大家玩殺馬特是為了什么,就是為了開心,沒有信仰也沒有什么規劃。”
殺馬特并不復雜,他們沒有什么要宣揚的主義。導演李一凡在演講中提到的,“沒有精彩的殺馬特,只有貧乏,生命極其貧乏的殺馬特。”他們能把玩的,只有他們的頭發。
在今天,我們以為殺馬特已經消失了,其實可能并沒有,不管是夜晚的殺馬特派對,還是連頭發都不玩的三和大神、隱居鶴崗的年輕人、脫口秀青年,他們都從未消失。
(文中刺猬、章魚、麗莉、魷魚為化名)
參考資料:
1.《殺馬特我愛你》李一凡
2.《李一凡:我拍了殺馬特》一席
更多精彩內容,關注鈦媒體微信號(ID:taimeiti),或者下載鈦媒體App

鈦媒體 App
13965篇文章TA的動態
2022-09-14 鈦媒體 App發布了 《星巴克加碼中國市場,未來三年要新增開3000家門店|鈦快訊》的文章
2022-08-11 鈦媒體 App發布了 《白云山麾下公司虛抬藥價“把戲”,被拆穿了》的文章
2022-07-06 鈦媒體 App發布了 《為了幫00后卷王找到工作,簡歷修改師們拼了》的文章
2022-07-06 鈦媒體 App發布了 《威尼斯向游客收“進城費”,國內城市如何借鑒?》的文章
2022-03-25 鈦媒體 App發布了 《蔚來2021年財報發布:年營收361億元,整車毛利率達到20.1%》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