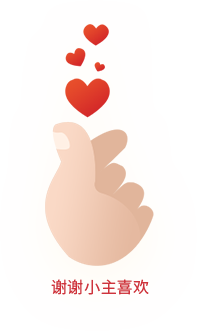兒童市場沒有永遠的“童話大王”
文 | 錦鯉財經(jīng)
如果要說童話歷史,其實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線。大概沒有人會想到,最初的童話創(chuàng)作居然是來源于一群貴婦們的茶話會。
路易十四統(tǒng)治后期,無聊的法國婦女們喜歡舉辦茶話會來消遣時光,由此展開了深遠的童話創(chuàng)作活動。1690年,茶話會里的一些故事開始陸續(xù)發(fā)表,其中最出名的《仙女的故事》與《新童話故事集》里一共收錄了25則童話故事與3個冒險奇幻故事。
拿破侖前時代,也就是戰(zhàn)亂時期的歐洲,一些民間的童話故事與傳說開始口耳相傳。那時候的童話基本都逃不開濃重的暗黑因素,殘缺的生活背景之下帶著復(fù)雜的人性思考,彼時的童話在某種程度上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童話產(chǎn)業(yè),但不可否認,這個產(chǎn)業(yè)的開局開得很漂亮。
直到1744年,英國兒童文學之父John Newbery出版了第一本兒童讀物《美麗的小書》,這本書融合故事、游戲、插畫,秉承兒童內(nèi)容“快樂至上”的原則,一舉打破了原本流行多年的黑暗風。
19世紀以后,作家們開始意識到兒童世界的主流意識始終圍繞真愛與美好。1812年出版的《格林童話》,里面200多篇故事就被改了40多次,修訂了7版才變成現(xiàn)在我們所看到的劇情,自此童話市場開始蓬勃發(fā)展,風格也一變再變。
說教的、怪誕的、奇幻的、浪漫的……如何怎么變化,童話始終存在。
中國童話產(chǎn)業(yè)沉浮錄
國內(nèi)的童話產(chǎn)業(yè)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發(fā)展得都比較矛盾。一方面是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蘊提供源源不斷素材靈感,例如在《中國童話史》就從30多本古代文獻中提取出神筆、燕子國、魚骨小人兒以及鼻孔里的樂神等多個經(jīng)典童話人物形象。
《搜神記》《太平廣記》《酉陽雜俎》里除了大眾熟知的神話傳說,對標小兒群體的童話故事也比比皆是,如果從初代童話起源算起,國內(nèi)的童話文學相比國外只早不晚,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國在兒童教育上一直頗為優(yōu)越。
明代時期,甚至出現(xiàn)了一部兒歌專輯《演小兒語》,這本書累計收錄兒童歌謠46首。但國內(nèi)兒童文學很長一段時間處在令人誤解的蕭條狀態(tài),事實上,蕭條的不是內(nèi)容,而是系統(tǒng)化的發(fā)展體系。
在1963年之前,國內(nèi)都沒有專門的兒童刊物,根據(jù)公開資料顯示,當時全國只有兩家專門出版童話的出版社。1963年,葉圣陶、冰心等作家逐漸意識到國內(nèi)兒童刊物的落寞現(xiàn)狀,在北京創(chuàng)辦了《兒童文學》。
此后的很多年里,《兒童文學》算得上是國內(nèi)童話產(chǎn)業(yè)的溫床與市場風向標,第一期就賣出了30多萬冊,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兒童文學》如此輝煌的背后,其實前期連刊號都沒有,整個編輯部只有3個人,就算后期人數(shù)最多時也只有12個。中間還因為一些外部因素停刊了十年,直到1977年才重新出版。
1978年,兒童文學界迎來了著名的“廬山會議”,彼時刊物的作家來稿終于活躍起來,據(jù)悉,當時《兒童文學》的主編徐德霞每天去郵局都要用麻袋來裝大量的稿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內(nèi)文學創(chuàng)作大爆發(fā),大街上隨便一個人都能吟誦幾句北島或者舒婷,文學雜志像潮水一樣鋪天蓋地涌現(xiàn)而來。
童話刊物趁著計劃生育的東風大幅度增長,在80年代時代,幾乎每個省都有自己的童話讀物。《兒童文學》作為產(chǎn)業(yè)鼻祖,發(fā)行量一度高達50萬。可惜好景不長,等到90年代,文學熱潮迅速降溫,下海經(jīng)商一波接著一波,所有文學刊物的發(fā)行量受到重挫。
童話讀物更是一波三折,從1991年開始,《兒童文學》的發(fā)行量就一路從50萬下滑到10萬以下,最慘淡的時候只有6萬。《朝花》《未來》《巨人》等大型童話刊物相繼停刊,當時兒童文學界有一句無奈的自嘲:“《朝花》凋謝了,《巨人》倒下了,《未來》不來了,《明天》還在明天。”
沒有辦法,得先生存下去。童話刊物單純只靠文字似乎注定做不成大生意,很多童話刊物在生存問題面前只能尋求轉(zhuǎn)型,幸好國內(nèi)的兒童消費市場有無窮的想象空間,做教輔、做作文選,要么扎根學校,要么綜合轉(zhuǎn)型,兒童大人雙手抓。
兩條路擺在面前,看似哪條都走得通。《兒童文學》選了后者,在1997年全面改版,不僅在一本兒童讀物上印著“9歲到99歲閱讀”的字眼,還將定價從3.5提到了5塊錢。不可否認,這種轉(zhuǎn)變帶來商業(yè)效應(yīng)有目共睹,根據(jù)調(diào)查顯示,1997年的《兒童文學》利潤從原本的二三十萬瞬間飆升到五十多萬。
主攻學校的也有不少,例如數(shù)次入圍童書作家榜單的曹文軒,2018年曹文軒在童書銷售方面的收入就高達2700萬,童書作家榜第一名楊紅櫻的版稅高達5600萬,是劉慈欣的3倍。但這兩條路的風險也很明顯,內(nèi)容轉(zhuǎn)型之后,成人與兒童之間的話題尺度不止一次發(fā)生沖突。
楊紅櫻的《天真媽媽》被視為誘導(dǎo)自殺而下架,沈石溪的《狼王夢》被指責對動物的性描寫尺度過大,冒險小說《查理九世》因為孩子模仿其中的暴力行為被禁,童話大王鄭淵潔更是被撒貝寧在《今日說法》上直指少兒不宜。
校園業(yè)務(wù)如火如荼,質(zhì)疑也從來沒有停止,鄭淵潔就曾在微博公開炮轟老冤家曹文軒。可以說,國內(nèi)的童話產(chǎn)業(yè)發(fā)展到現(xiàn)在,遺憾的是行業(yè)系統(tǒng)遲遲沒有形成。2000年以后,兒童文學再次被時代與市場選中。
根據(jù)開卷圖書調(diào)查顯示,2012年我國兒童圖書的市場增速高達4.71%,《兒童文學》在2009年的發(fā)行量突破了100萬。市場銷量不愁了,內(nèi)容卻在頻頻踩中尺度紅線后開始變得畏手畏腳,2009年,《兒童文學》一邊發(fā)行大增,一邊卻被讀者在豆瓣上質(zhì)疑內(nèi)容越來越敷衍。
2016年,一條指責《兒童文學》內(nèi)容越來越低齡無腦化的微博引起網(wǎng)友1萬多條轉(zhuǎn)發(fā),3000多條評論。風風雨雨五十多年,國內(nèi)的童話產(chǎn)業(yè)在內(nèi)容與市場兩個維度之間不斷沉浮掙扎,免不了此消彼長,而突破不了內(nèi)容桎梏,似乎上整個童話圈最大的痛點。
多面性的童話生意不好做?
童話被質(zhì)疑低齡化,這個邏輯或許聽上去很不可思議,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隨著年輕群體步入婚姻,升級成為父母,相比老一輩的快樂至上原則,他們往往更加偏向于在娛樂中實現(xiàn)各種意義上的教育,這就意味著過于平淡的內(nèi)容勢必無法在教育中,引起父母位置上的共鳴。
事實上,這些年來,童話市場逐漸變得蓬勃起來,除了傳統(tǒng)的圖書形式,整個生意鏈都在不斷更新。以鄭淵潔的皮皮魯公司為例,童話大王的公司主營業(yè)務(wù)早就從早期的圖書出版發(fā)展成了出版、新媒體、動畫影視以及IP授權(quán)四大領(lǐng)域。
看起來每個領(lǐng)域的想象力都不可小覷,例如動畫產(chǎn)業(yè),根據(jù)數(shù)據(jù)顯示,2018年全年的兒童動畫片中,童話題材以217部的數(shù)量占總體的49%,幾乎一半。無獨有偶,2021年上半年的動畫片題材中,童話題材的數(shù)量高達104部,與教育題材加起來有183部,占比超過64%。
童話生意之所以能迅速分裂,原因很簡單。從獨生子女時代過渡到如今的二胎、三胎時代,國內(nèi)的兒童消費市場注定只增不減。2016年,我國新生兒數(shù)量超過1750萬,2018年,中國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0-14歲的兒童數(shù)量達到2.5億人。
三胎政策放開之后,站在兒童消費紅利上守望與奔跑的機會無疑更多了,消費市場也帶來了真金白金的實質(zhì)輸出。騰訊實驗室曾經(jīng)發(fā)布過一項調(diào)查,我國的兒童消費市場已經(jīng)超過4.5億,尤其在育兒方面,一個家庭全年的育兒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22%。
然而,動畫、音頻等新童話輸出形式雖然調(diào)動了整個產(chǎn)業(yè)的鮮活,但也側(cè)面擠壓了童書在整個家庭育兒消費中的存在感,據(jù)悉,有92.9%的家長會為孩子購買童書,可是年平均花費金額只有113.22元。
反觀動畫或者音頻,根據(jù)統(tǒng)計,在過去十年里,國內(nèi)動漫票房最高的30部影片中,兒童題材占了22部,占比高達74%。2020年,兒童有聲閱讀市場達到78.3億的規(guī)模,根據(jù)第十六次全國國民閱讀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0到8周歲兒童的聽書率達26.8%,同比上漲29.5%。
不得不承認,童話市場依賴純文學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復(fù)返,正如皮皮魯公司立志想要成為中國童話界的“漫威”,童話經(jīng)濟的多面性正在日益凸顯。
可奇怪的是,國內(nèi)的童話IP影視化并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輝煌,就連多少人童年時代的白月光《舒克和貝塔》在最初播放的時候也曾經(jīng)歷重重質(zhì)疑,這并不是小道消息,畢竟鄭淵潔公開證實過,當年有1600多名讀者來信,其中99%是對《舒克與貝塔》的不滿。
無獨有偶,不少經(jīng)典童話IP被影視化時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2007年,中國電影集團、香港先濤電影聯(lián)合迪士尼出品《寶葫蘆的秘密》,最終的票房卻只有70萬。2014年,同樣有迪士尼加盟的《神筆馬良》票房不到6000萬。
改編自國內(nèi)經(jīng)典作品《查理九世》的《墨多多謎境冒險》因為題材尺度問題在2018年被定檔又撤檔,即便是三年后的今天依舊處于查無此片的狀態(tài)。8月份,原本定檔的皮皮魯系列《罐頭小人》再次宣布延期,童改IP命途多舛。
有意思的是,作為童話大王最有名的IP系列,《罐頭小人》前幾天的超前點映只有不到200萬,貓眼想看畫像中顯示,想看《罐頭小人》的用戶群體中主力軍竟然不是兒童群體,而是看著鄭淵潔的書長大的80后與90后。
如今的小孩們不認識舒克貝塔,也沒見過楊紅櫻的馬小跳與曹文軒的草房子。距離《舒克貝塔》的播出已經(jīng)過去二十多年,看過94年《魔方大廈》的人也慢慢成了父母,這期間,再也沒有一部童改IP復(fù)制曾經(jīng)的輝煌。
取而代之的是奔跑在青青草原的羊群,東北森林里出沒的熊大熊二,以及在水坑里打滾的佩琪。不能說有什么遺憾,只是當傳奇過的中國童話面臨斷代,誰都忍不住一聲嘆息。
當代兒童失去閱讀興趣了嗎?
當在老家里看到四歲大的侄子趴在沙發(fā)上刷抖音,蓓蓓的第一反應(yīng)是震驚,“我都懷疑他能不能看懂!”但意識到當代年輕人基本都是雙職工,孩子扔給父母帶,往往一部手機就能讓一個熊孩子安靜一下午的時候,蓓蓓才明白過來,這或許是當代兒童最常見的狀態(tài)。
根據(jù)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中心最新統(tǒng)計顯示,低于10歲的網(wǎng)民超過1800萬,2015年,有56%的兒童初次上網(wǎng)的年齡低于5歲,很多孩子對手機平板的了解甚至要超過父母。網(wǎng)上有一個段子,解決熊孩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給他一部手機。
《2019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未成年人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經(jīng)常收看短視頻的比例達到46.2%。在3000多個調(diào)查樣本中,有76.3%的兒童在小學階段就開始接觸網(wǎng)絡(luò)游戲。
互聯(lián)網(wǎng)固然拉近了兒童與這個世界真實的距離,但各種錯綜復(fù)雜的信息正在以變異的、扭曲的方式層層疊加,一點點靠近原本純凈的童話的世界。或許這不是任何人的本意,可往往事態(tài)并不受主觀控制。
在算法產(chǎn)出的即時快樂中,即便是一則他們看不懂的視頻也能迅速取代曾經(jīng)的白雪公主與辛黛瑞拉。何況兒童并沒有什么辨別能力,有調(diào)查顯示,只有兩成多未成年人在短視頻看到不良信息會質(zhì)疑或者舉報。
可想而知,書籍的存在感正從這屆兒童的生活娛教中慢慢變淡。不像八九十年代的兒童除了每天定點等待動畫片播放,只能將課外情感寄托在童話書,小人書,連環(huán)畫上。
畢竟不管是娛樂還是學習,這屆兒童所能選擇的模式太多了。CSM的報告顯示,CCTV-14和金鷹卡通這兩家少兒上星頻道的收視份額都曾力壓湖南衛(wèi)視。
紙質(zhì)書慢慢變成了電子閱讀,商業(yè)宏觀數(shù)據(jù)也從側(cè)面印證了這一點,喜馬拉雅在聽書領(lǐng)域開辟了專門的“親子事業(yè)部”,還推出獨立的兒童音頻APP;蜻蜓FM在兒童音頻內(nèi)容投入1.5億元;“凱叔講故事”已完成四輪融資,融資總金額超2.6億元。
這不由得讓人懷疑,當代兒童是不是已經(jīng)失去了閱讀興趣?
其實也不然,因為依然有52.3%的兒童家長認為“紙質(zhì)書籍”最適合兒童閱讀。2014年一項針對1500多個家庭的調(diào)查顯示,2~10歲孩子的父母中有一半表示,他們不允許孩子使用電子閱讀。
2016年,一項針對1500名家長的類似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35%的家長抵制數(shù)字閱讀,因為他們擔心孩子沉溺于純單向輸出的數(shù)字閱讀模式,會失去對紙質(zhì)閱讀的興趣。
也就是說,一本承載幾代人喜怒哀樂的童話書不管在什么年代,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就算是各種娛樂方式已經(jīng)開始大肆搶占兒童市場,誰的童年都需要一個“皮皮魯”,可遺憾的是童話世界沒有永遠的“鄭淵潔”,這一代到下一代,或許不是觀念在變,而是市場在變。
更多精彩內(nèi)容,關(guān)注鈦媒體微信號(ID:taimeiti),或者下載鈦媒體App

鈦媒體 App
13965篇文章TA的動態(tài)
2022-09-14 鈦媒體 App發(fā)布了 《星巴克加碼中國市場,未來三年要新增開3000家門店|鈦快訊》的文章
2022-08-11 鈦媒體 App發(fā)布了 《白云山麾下公司虛抬藥價“把戲”,被拆穿了》的文章
2022-07-06 鈦媒體 App發(fā)布了 《為了幫00后卷王找到工作,簡歷修改師們拼了》的文章
2022-07-06 鈦媒體 App發(fā)布了 《威尼斯向游客收“進城費”,國內(nèi)城市如何借鑒?》的文章
2022-03-25 鈦媒體 App發(fā)布了 《蔚來2021年財報發(fā)布:年營收361億元,整車毛利率達到20.1%》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