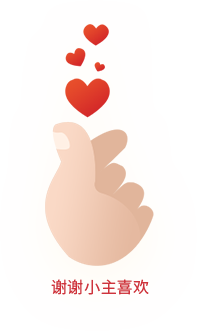中國潮玩起步,年輕沒有標準答案
文丨奇偶派,作者丨田歡子,編輯丨王十
隨著地下街頭文化的消退,日本、歐美等國家和地區走過了潮玩的高峰期,消費者人數平穩,在圈層里自娛自樂。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盲盒迅速走紅,與此同時,潮玩“概念”也在內地迅速火起來,各類潮玩生意發生質變,正式變成了IP類消費品生意。
中國目前的人口結構中,消費主體正在改變。15-39歲的回聲嬰兒潮一代逐漸成為社會的消費力量,這個代際人群具備強烈的消費欲望,“個人化”悅己型需求成為新的消費變化。在這種背景下,亞文化得以有機會沖到主流文化前面。
盲盒的走紅如星星之火,點燃了大眾對潮玩的熱情,炒鞋、炒盲盒、炒手辦等隨之成為熱門潮玩方式。
2020潮玩行業深度報告預測,以日本2020年滲透率為基準,測算15-39歲核心受眾圈層的空間,預計2020/2025/2030年中國衍生零售市場規模為363/659/1171億元,衍生零售加上改編娛樂市場規模為639/1021/1938億元。
被盲盒點亮的潮玩行業,成為資本新的流向。潮玩落地中國,它又將該如何被市場定義?
火熱拍賣進行時
消息停留在一個粉色兔子頭像這里,她在群里詢問了泡泡瑪特娃娃的交換信息。“labubu向日葵和dimoo雙子換labubu梵高,玫瑰那個骷髏和dimoo天秤的有沒有哇。”但不再有人回應她。
這個由195人組建的“一起開心拍賣群”,無間歇地刷屏了近1.2萬條消息后,終于在深夜23點12分沉寂了下來,但拍主阿星此刻還很忙,她要抓緊時間趕在天亮之前,將這些被拍下的娃娃全部整理好,以便明天發往全國各地,時間很緊,娃娃很多,她來不及清點有多少,而這些娃娃,全部都是她玩盲盒抽到的。
差不多4個小時前,群里剛舉行了一場異常火爆的線上拍賣會,時長約3個小時。
19點29分,約拍員Rubi艾特所有人,“今晚的拍賣開始啦!”Rubi發布的公告上標明:娃娃比較雜,基本上每個系列就一兩個,價格除了部分熱款,其他款式5+2起拍……公告中還預告了明晚八點半的拍賣預告品。
公告發完,阿星發了一張今晚要拍的娃娃全景圖,圖中擺滿了密密麻麻的娃娃。
“開始了”,阿星通知大家,“來了來了”,很快有人應和,接著阿星發了個小禮物,告訴大家“扣1”,群里瞬間火熱起來,滿屏的1刷起來,氣氛開始點燃,兩輪小禮物送完,拍賣正式開始了。
“黑管家5起+2”,一秒不到,有人出價20元,一分鐘后,阿星從45元開始截價,有人又開始往上加,就要落在50附近了,“54一次、54兩次、54三次”,最終,這款娃娃落價在54元。群里有人感嘆起太低了,“姐妹忒實在了,別的基本都是60往上走拍下來的。”
拍賣持續火熱進行中,大約每兩分鐘,阿星就有一個娃娃被異地娃友拍走。
24歲的Rubi是第二個進入這個群里的,因為都喜歡盲盒娃娃,她和群主在網上結識為朋友,“一開始就是她想弄拍賣,她抽得娃多,就建群了,她拍完之后很多朋友也想搞,就留著了。” 在拍賣進行時,不斷有娃友從微博超話尋來,還有被朋友拉進來的,目前,這個群人數還在往上增加。
拍賣群的分工并不明確,甚至有些隨意,但建群以來,也舉行快10次了,Rubi說,拍賣是不定期舉行的,但會提前預告,只要有娃友有多余的娃想要出手,找她預約就行。而聚到這里的娃友,他們手里都囤有不少娃,久了不想要了,或者重復的,平時自己賣又比較麻煩,來到這里,就可以一次性全賣了,“放著也是放著。”
Rubi發現,群里拍賣均價都有點低,除非是熱款,或者是絕版的,會比原價高,但也不會高出很多,普遍在10-20元范圍內,在Rubi看來,其實買賣盲盒娃娃是虧本的,但她還是很享受抽盒的樂趣,在她的房間里,已經住著100多個盲盒娃娃,這百來只娃娃里,喜歡的她都已經擁有了,所以她最近已經不怎么買了,除非再遇到喜歡的。
一位資深盲盒玩家告訴奇偶派,類似這種圍繞盲盒娃娃展開拍賣游戲還有很多,而在Rubi眼中,這種拍賣群挺好玩的,天南海北的娃友聚在一起,沒有利益往來,只是單純地交換多余的娃娃,平時也不用一直盯著,花費的時間也不多,空閑之余,她只需幫忙寫寫公告通知人,有空就看看群。
在微博上,某款盲盒的單一話題就已經達到了5.7億的閱讀量,發布的帖子累計有12.2萬條,已經超過了一些當紅明星的流量。
從凌晨到深夜往復循環,這里“出娃換娃”的交易信息幾乎沒有間斷過。
冒著巨大的風險,鼓起極大的勇氣,幾乎砍掉其他所有品類,只留下盲盒的泡泡瑪特,幾乎憑借一己之力“定義”并帶火了中國潮玩市場,而在Rubi眼中,抽盒換娃只是喜歡,看著好看,更不會在意這些娃娃出自于某設計師之手,在她看來,潮玩沒有什么定義。
這些3-4寸大小的娃娃,有乖巧可愛的,也有怪誕逗趣的,但它們都不承載任何故事內容和價值觀,而年輕娃友之間盛行的交易游戲,似乎正在為這些娃娃賦予新的含義,一種社交關系里,無法定義的“軟通貨”。
潮玩是個圈
盲盒娃娃的價值盡管特立獨行,卻又和“敗家”的手辦有一些共性。
學生時代開始癡迷動漫、各地參加漫展、開始買手辦,手辦愛好者幾乎都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李奇也是這樣過來的。作為12年的重度手辦愛好者,如果有十分的喜愛度,他給自己打9分。
現在,他家里的柜子里擺滿了各個角色,海賊王、輕音少女、dc貓女、歐比旺、saber……各式日本、歐美人物角色,只要是喜歡的,價格合宜,他都會買下來,拍一些漂亮的圖,然后放進專門的陳列柜里,放不下了,就留在包裝盒里,甚至不拆也行。
手辦的市價變動大,漲漲跌跌很正常,李奇買入的貓女600多,現在已經跌了,而買過最貴的一個是2000,“一個比較誘惑的女性角色,我甚至都沒拆封,賣了3900,那款倒真是圖個新鮮,其實也不是什么了解的角色,可能有些沖動。”不久前,他在網上關注了一款滅霸,做工挺好的,之前預訂2000多,但隨著復聯熱度的散去,已經崩值了一半。
95后玩家剁手力數據顯示,手辦類別消費同比上升了189.7%,成為最受年輕人歡迎的消費產品。
李奇說,產品的人氣、出貨量、限定品、商家和玩家的炒作會影響產品的價格。而在手辦和玩具圈里有個詞,“眼緣”,幾乎決定著玩家是否購入。
在李奇看來,不管是手辦,還是盲盒,這些玩偶都是普通的工業流水產品,算不上藝術品,但只要玩家喜歡,這些都不重要,角色一旦買下來,就會有一種二次元進入三次元的奇妙反應發生。常常下班回家很累了,李奇就會打開柜子,站在這些人物前細細打量,有時聯想到其中劇情,開心到沉浸進去,疲倦便會一掃而散,常年來,這些手辦如流水般滲入李奇的三次元世界。
相比最初一兩年時候的開心,這幾年,李奇對手辦的熱情有些消退,手辦的價格正在變貴,以前9800日元能買到一款品相不錯的手辦,現在很多都需要20000日元,所以現在他更看重手辦的價格,做工、眼緣、品牌的重視程度則依次遞減。
擁有的手辦越來越多,疲勞值在上漲,收集的欲望還增添了些額外的煩惱。畢業以來,他搬了三次家,一次比一次麻煩,多了沒地方擺放,家人勸他少買點,他也只是“嗯”一聲應付,不會往心里去,他并不想退圈,即使當初一起玩的很多人都退坑了,自己的熱情也在減退,但他還是想當作一個興趣愛好保留下來,他抑制這種消退的方法是,減少買的頻率。
以前讀書的時候,李奇經常跑去上海看展,每一屆的CCG(中國國際動漫游戲博覽會),他都會不會錯過,上班后越來越忙,現在已經4年沒去了,但今年,他決定去Wonder festival上海和上海國際潮流玩具展看看,“這倆都是玩具,前者手辦,后者潮玩。”
李奇并不明白手辦和潮玩的區別是什么,“這種下定義的東西,爭議太大,其實我不太理解潮玩。”
曾經的炒鞋玩家周彪也不太明白,潮玩到底是什么?“我有時也驚訝,這玩意為啥炒這么貴。”
大學是個愛好培養基地,周彪也是大學那會兒喜歡看NBA,“球星穿的球鞋特別好看”,一畢業一工作,周彪就開始為愛好買單了,從一雙比較普通的籃球鞋開始,再到后來的AJ,再到直接讓線下導購員拉入微信群,就這樣,18年起,他開始進入“鞋的世界”。
群里有活動會有通知,他就會去搶,到2019年,他開始大量囤鞋,“陸陸續續買了十幾雙,花了兩三萬。”買入后,他心想著應該能賺點,便把鞋放在炒鞋平臺上,半個月過去了,沒賣出去一雙,鞋過時很快,又無人理睬,從20年中旬開始,他決定放棄炒鞋。
后來周彪懷疑,炒鞋應該是門產業鏈,相比他這樣的小散戶,那些專業的炒鞋機構和平臺綁定得更深,散戶拼不過集體,“他們一批貨一上架肯定是優先賣他們的。”而在線下門店,周彪發現,這些門店會不定期賣一些市面上買不到的鞋,限量的饑餓營銷之下,大家就會去搶,“實際上根本搶不到的,就只能去那些炒鞋平臺或者是其他一些門店去購買。”
交了兩三萬的學費后,周彪決定腳踏實地做好自己專業領域的事情,“炒鞋對于個體,是真的很不賺錢的,除非你在耐克或者阿迪官網上,新鞋出來抽簽,抽到一雙特別好的鞋,你才會去賣到好的價格,以后我不會炒了。”
年輕人會慢慢長大,但總有年輕人,炒鞋、手辦、盲盒……,這些專屬于年輕一族的潮流愛好,正在被“潮玩”一詞打開想象的翅膀,而潮玩是什么,大多數沉浸其中的玩家仍然沒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然而,資本市場對潮玩市場的想象空間已經被打開。據天眼查顯示,截至今年11月30日,中國內地新增了260余家潮玩相關企業,總量至少達到800家。除泡泡瑪特外,還有52Toys、IP小站、IPSTAR潮玩星球等品牌也獲得了資本市場的青睞。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潮玩零售市場規模約207億元,預計2024年將增至763億元。另一個數據同樣說明問題。2019年,中國GDP增速為6.11%,同年,潮玩市場的增速是47.86%。TOPTOY創始人兼CEO 孫元文認為,“當一個市場增速跑過GDP增速兩倍還多,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藍海行業。”
未被定義的軟通貨
盲盒打響了這片黑暗森林里的第一槍,用“弱IP-強渠道”打開了一個關于“IP類消費品”的中國戰場,此后,“潮玩”一詞被廣泛提及。
據了解,潮玩的原意是Art Toys或Designer Toys,即藝術家玩具或設計師玩具。但實際上,在內地迅速火起來的“潮玩”概念,已經經歷過了本土化的“改造”,朝著“中國式潮玩”的方向進化。
與日本依托動漫產業、美國依托電影產業壯大的成熟IP泛娛樂產業比較,中國還處于牙牙學語的快速發展階段,國內的潮玩或IP類消費品市場仍不是一個充分競爭市場,已經顯現出的玩家在其中的市場份額依然有限。
數據顯示,2019年潮玩市場規模207億元,泡泡瑪特營收17.6億元,市占率8.5%。第2-5名市占率分別為7.7%(歐洲公司)、3.3%(香港公司)、1.7%(日本公司)、1.6%(美國公司)。頭幾個玩家市占率的差距沒那么大。
據浙商證券研報,以美國2019年度數據,測算成熟業態的大空間,經測算預計針對中國全年齡成熟業態的IP改編影視娛樂及衍生品零售、主題樂園分別對應4203億元和4265億元,整體IP衍生市場空間為8467億元。
巨大的市場空間誘惑下,市面上的企業玩家們試圖搶先定義何為“中國式潮玩”。
此前,定義國內潮玩,一定繞不開的就是泡泡瑪特,它靠其核心產品盲盒走出來,在小眾消費“破圈”、迎來規模增長之前提前布局,這是它成功走到今天的秘密之一。
但是,外界對其做的是盲盒生意還是潮玩生意的質疑未曾斷絕。泡泡瑪特CEO王寧這樣對外解釋,自己做的是潮玩生意而非盲盒生意,他認為,盒內的“Molly”等形象就是潮玩,這些形象具有IP屬性,雖然是一種與傳統IP不同的無內容、無故事的形象化的IP,但同樣具有陪伴價值,而這種陪伴的價值,需要購買者在購入之后自己賦予其意義,而盲盒本身,只是作為一種營銷和銷售手段。
但是,泡泡瑪特對國內潮玩的定義能量在降低。在這樣一個代表未來可預見的巨大市場,不少競爭者前來搶占份額。
線下零售TOP級玩家名創優品推出的獨立子品牌TOPTOY,定位于潮玩集合店,TOPTOY試圖對泡泡瑪特的強渠道一側出擊。需要正視的是,在國內目前市場上弱IP的情況下,渠道之爭仍然是今天潮玩市場競爭的重點,TOPTOY的出現很有可能是對現在的泡泡瑪特最有挑戰性的一個競爭者。
對于潮玩的定義,TOPTOY創始人兼CEO孫元文不認為泡泡瑪特做的是潮玩生意,“盲盒只是潮玩的其中一個品類,任何一個單獨品類都不能代表潮玩”。孫元文理解的潮玩,是“帶有內容和價值觀的IP衍生品”。
然而事實是,這些沒有內容和價值觀的產品在盲盒這種營銷手段下,生長出了全新的內容和價值觀,數位盲盒愛好者告訴奇偶派,這些娃娃設計可愛,不同系列有不同特色,抽盒帶來的刺激和驚喜,會增添得到娃娃的意義,而一旦擁有了這些娃娃,就會產生類似和寵物之間的情感,此外,她們并不會在意這些娃娃是否出自名設計師之手,自己喜歡最重要。
盲盒和產品,似乎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賦予誰故事和內容,而單看盲盒領域,據頭豹研究院數據表明,2019年中國盲盒市場規模預測值為28.8億,如果這個數據誤差不太大,那代表泡泡瑪特在盲盒領域的市占率為47.2%(2019年泡泡瑪特盲盒營收13.6億元),遠超其它潮玩競爭者。
而不管在盲盒、手辦,還是炒鞋領域中,不難發現一個規律,互動或是游戲伴隨著過程產生,特有抽盒+玩家之間類似拍賣炒玩,手辦和炒鞋也有炒賣的流通市場,這種帶著“IP”流通互動的屬性,會不會又是“中國式潮玩”的隱性基因呢?
不一的軟通貨玩法,目前尚不能被一錘定義,它正在等待市場的挖掘。
寫在最后
機會尋覓者聞風而動,紛紛向潮玩領域聚集,陌生的創業者和投資們站在這個“潛在風口”前發問,潮玩是什么?應該怎么玩?
迷茫的檔口,大部分玩家或許會對標萬代,挖掘IP持續變現;對標樂高,沉淀獨有的“語言”體系;對標迪士尼,將優質IP商業價值最大化。
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王寧過去總說,泡泡瑪特要做“中國的迪士尼”,現在說法變了,他喜歡用唱片公司來類比。孫元文在運營TOPTOY的過程中,參考最多的學習對象則是萬代。
在這些“標準答案”之下,潮玩在中國,又有沒有另一種玩法?
中國與日美的IP泛娛樂產業鏈條有很大不同,國內潮玩行業露出冰山一角,隱喻的是觸礁還是藍海,這些還不得而知,但潮玩,又可不可以解釋為“潮品”和“玩法”的結合體呢?
注:文中Rubi、阿星、李奇、周彪為化名。
更多精彩內容,關注鈦媒體微信號(ID:taimeiti),或者下載鈦媒體App

鈦媒體 App
13965篇文章TA的動態
2022-09-14 鈦媒體 App發布了 《星巴克加碼中國市場,未來三年要新增開3000家門店|鈦快訊》的文章
2022-08-11 鈦媒體 App發布了 《白云山麾下公司虛抬藥價“把戲”,被拆穿了》的文章
2022-07-06 鈦媒體 App發布了 《為了幫00后卷王找到工作,簡歷修改師們拼了》的文章
2022-07-06 鈦媒體 App發布了 《威尼斯向游客收“進城費”,國內城市如何借鑒?》的文章
2022-03-25 鈦媒體 App發布了 《蔚來2021年財報發布:年營收361億元,整車毛利率達到20.1%》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