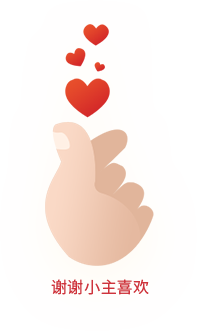睡眠經濟真相:年輕人如何重金買覺?
這天晚上,原本11點就已經躺到床上的劉可,直到2點才正經睡著。在她看來,白天的生活不屬于自己(屬于工作),晚上一定要搶回點屬于自己的時間。
于是,每天晚上即便躺到床上,她也總還有一堆事情要忙:看書、追劇、看電影、購物、敷面膜、打游戲。
或許你也有過這樣的時刻——夜深了,但為了抓住一點點時間的尾巴,即便躺在床上也仍不愿放下手機;也可能是這樣的場景,在幾乎全黑的辦公大樓里,一個人坐在電腦前加著班;又或許是這樣的場景,路燈下約上二三好友,吃著夜宵、喝著啤酒……
人的一生,本應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會在睡眠中渡過。然而,手機使用頻率的劇增、越來越常見的996工作制、夜生活的豐富多彩,正讓睡眠時間被逐漸壓縮。越來越多人變得像劉可那樣,從本該屬于睡眠的時間里,抽出一些讓它“屬于自己”。
調查數據顯示,從2013年到2018年,中國人的平均睡眠時長從8.8個小時降至6.5個小時。這意味著,過去五年間,我們活生生從自己的睡眠時間中偷出了170余天的清醒時間,分派給忙碌的工作和生活。
不管是主動熬夜還是被動失眠,毋庸置疑的是,睡眠問題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時代病”。
中國睡眠研究會發布的一組數據顯示,中國成年人失眠率高達38.2%,超過3億中國人有睡眠障礙。而在行業人士看來,這一數據或許還在被低估。“睡眠困擾的群體應該不止這些,80%以上的人群多多少少會有睡眠困擾”,這是有著16年心理咨詢經驗的鄒鄒作出的判斷。
繼“車厘子自由”、“豬肉自由”后,“睡眠自由”成為當代人的新一輪期待。從褪黑素、助眠噴霧到乳膠枕、智能床墊,再到各類促進睡眠或監測睡眠情況的App,花樣繁多。
當一夜好眠成為奢侈品,睡眠經濟也正當其道。看似“昂貴”的睡眠市場,對于企業來說是否就意味著金礦?
那些睡不著的90后們
小方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睡過一個好覺了。
今年28歲的她在廣州一家新媒體機構負責內容創作,工作所具備的特性,讓她不得不保持高密度的信息接收和攝入水平,“一直很焦慮,如今夢里都是選題和工作”。昨晚,為了追趕deadline,夜半兩三點她還在加班加點寫稿子。
同一時間,1400公里之外的上海,林琳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耳機里助眠的雨聲已經停了很久了,睡意卻始終沒有醞釀成功,白天工作上的糟心事像電影一樣在腦子里閃回,她干脆拿起了手機,看起了之前還沒讀完的電子書。
像是回到了一年前。彼時,大學畢業的她剛剛入職第一份工作不久,全新的環境、與大學專業并不契合的工作性質、復雜的同事關系、無情的KPI考核,每一樣都壓得她喘不過氣,那時,她也像現在這樣,成宿成宿地睡不著覺。
一邊焦慮,一邊睡不著。同樣的情況存在于無數個和小方、林琳一樣的90后身上。
2017凱度健康國民健康調查(National Health and Wellness Survey,2017)的數據顯示,2010到2017年間,18-29歲的中國年輕人中越來越多人面臨失眠困擾,失眠人群的比例從42%增長到59%。這一比例甚至高于老年群體——53%的74歲以上成人有失眠問題。
繼脫發問題“長江后浪推前浪”后,90后又不幸中招,成了“特困戶”。
不過,劉可顯然跟小方、林琳不大一樣,她也焦慮,但不是由于工作壓力,而是對時間缺乏足夠的自主支配權力,用她自己的話說,更多時候她其實是“舍不得睡”。
“下班吃個飯,到家差不多就是九十點鐘了,洗漱、收拾完,一看已經12點了”,劉可感慨,時間過得太快了,也許0點以后才是自己的時間,因此“就算再困,躺到床上,也要刷刷微博,看看視頻再睡”。
出于這種心理陷入這種晚睡漩渦的人,也絕不止劉可一個。
年初,“報復性熬夜”一詞在網絡上爆紅,用來專指那些“白天過得不好或者過得不滿足,想借夜晚時間找到補償”的人,很多年輕人瞬間找到了共鳴。
“除了焦慮、環境引起的失眠,這其實是剛剛出現的一個問題,而且這部分群體主要是95后。”鄒鄒也發現了這一趨勢,她解釋道,這就是所謂的“補償機制”在發揮作用,但這種作用并非持久的。
后遺癥往往在第二天就出現。“與其說是‘報復性熬夜’,不如說是‘透支性熬夜’,熬完后第二天工作遲到、工作精力也不夠,所以工作時間延長,然后報復自己?”有人對此直言。
時間長了,劉可也有感知。前幾天,她突然發現,年紀輕輕的她,眼角已經出現了幾條細紋,為此她不得不在購物車加購了價值不菲的某品牌眼霜。
北上廣深最失眠
許多年前,科比一句“我知道每一天凌晨4點洛杉磯的樣子”,曾讓無數人為他的努力與堅持動容;而現在,凌晨四點的北上廣深,卻更多戳中的是年輕人的辛酸與無奈。
老家潮汕的林琳大學畢業后輾轉廣州、北京,暫時留在了上海,但對于眼下看似安穩的生活,她始終有一種不確定感,她總覺得缺了點什么。
潮汕人強烈的宗族、鄉土觀念以及對見識外面世界的渴望,這兩種情緒時常在她內心里撕扯、打架——她想過回家,“但老家沒有合適的崗位、機會”;她也想過留下來,但上海昂貴的生活成本讓她心生畏懼,房租、一日三餐、同事朋友間的社交……每一樁每一件都是開銷,更要命的是,上海或許也不是她內心里的那個“烏托邦”。
林琳的情況,其實是大部分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的縮影。他們懷揣著對大城市的憧憬和向往,在畢業后毅然投身城市的鋼鐵森林間,當血淋淋的現實給他們迎頭一擊時,他們想逃卻又離不開,巨大的壓力、高度緊繃的狀態讓他們無法入眠。
根據中國睡眠研究會發布的《2018互聯網網民睡眠白皮書》,北上廣深睡眠問題用戶占比達60%,相比之下,其他城市這一比例為52%,其中,北京、上海、廣州日常睡眠時長均在全國整體平均線下。
現在,林琳的打算是找個二線城市的工作,但至于去哪,她也還沒有想好。
相比林琳的長期“動蕩”,在廣州工作3年后,小方終于下定決心要留在廣州了,連續考察了好幾個月后,11月中旬,她已經給南沙一個樓盤交了2萬的定金,就等樓盤開盤付全款了。
然而,有這樣一個長期固定的安身之所,能留在這座眾人夢寐以求的城市,并沒有緩解她眼下的失眠和焦慮。
為了籌集買房的幾百萬資金,父母已經拿出了他們的畢生積蓄,剩下的缺口要靠借款、貸款補足——新一輪的焦慮襲來,還款、父母未來的養老都壓在她肩上,她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生活,無法輕易離職、要拼命寫更多的稿子——她更睡不著了。
而在深圳一家智能睡眠硬件公司擔任聯合創始人、COO的龍亮臻則訴說著另一種失眠樣本。“我屬于焦慮型,長期反復失眠,算是深圳創業者的典范吧。”說起自己,龍亮臻頗有些自嘲。
上百號人的公司要養活,公司的市場運營、管理,融資的需求等等,再加上兒子、丈夫、父親多重家庭身份,晚睡、失眠已經是龍亮臻的家常便飯,他甚至長期養成了半夜發朋友圈的習慣。
這個號稱“全球創客之都”的城市,誕生了騰訊、華為、中興、萬科這樣的“巨無霸”領軍企業,繁育著千千萬萬的中小微公司,也吸引著一代又一代懷揣創業夢想的年輕人,而龍亮臻,也不過是這無數基層創客中的一位。
創業的壓力已經足夠巨大,還有時不時出現的同行猝死的消息,持續挑動著這些創業者的神經。“就在上個月,原來深圳科創圈的兩位朋友離世了。”說著,龍亮臻在微信上發來了一張群聊的截圖。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睡眠?
由于城市化發展與現代化進程更快,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早已面臨“失眠”這一時代病癥。各類睡眠書籍、助眠床品、安神飲料、催眠軟件紛紛涌入市場,《時代》周刊曾估算,美國和日本睡眠創業市場的規模已超千億美元。
現在,忙碌的中國人也開始后知后覺,漸漸意識到健康和睡眠的重要性,為了找回對睡眠這件事情的掌控權,年輕人們可沒少折騰。
趁著雙十二的優惠活動,小方在購物網站上下單了百元促銷價的泰國乳膠枕,在這之前,她還嘗試100多元一瓶的褪黑素,但對她而言助眠效果并不大,“我超量吃都不管用,可能要吃安眠藥吧”。
眼下,正嚷嚷著“乳膠枕也沒用,還是更喜歡舊枕頭”的她,正在思考“是不是換張更硬的床”——這也意味著,她至少還要再花費一千元。
而林琳為了能睡著,喝牛奶、泡腳、用蒸汽眼罩、換枕頭、中藥調理,市面上有的“土方子”基本都試過了;現在她更擅長營造睡眠的氛圍——打開床頭柜上的香薰燈,戴上立體環繞的藍牙耳機,播放起她千挑萬選的音樂,“不一定有用,但是一種心理安慰吧”。
林琳所說的的確是現今年輕人的普遍心態,不一定有用,但也總得試試,萬一有用了呢?為此,眼罩、隔音耳塞、泡腳盆、浴足劑、足貼、香薰香料、小夜燈、褪黑素、香薰蠟燭成為了年輕人購物車中常見清單,似乎沒有這樣幾件裝備,就不足以談失眠。
一個多月前,打著“提升全民睡眠質量”的旗號,馬云爸爸又從年輕人那撈了一大筆。
10月21日至31日預售期間,天貓國際上的褪黑素軟糖賣出超75000瓶,其中Vitafusion褪黑素軟糖超25000瓶,花王蒸汽眼罩賣出超75000盒,助眠泰國乳膠枕45000個,德國安爾悠睡覺專用耳塞賣出25000對。
這個月的雙十二,戰績想來也不會太差。淘寶上,多家主營保健品的海外旗艦店早在月初就打出“雙十二鉅惠來襲”的口號。
當億歐問起某家店鋪的褪黑素軟糖時,客服表示,89元60粒的褪黑素軟糖如今第2件半價,而據其介紹,這個去年才在天貓國際開設旗艦店的美國保健品品牌,僅上述褪黑素軟糖一項,每個月銷量可達到3000件。
曾連續幾年對中國睡眠市場有過調研的Sleepace享睡創始人黃錦鋒發現,過去幾年間,中國人對睡眠產品的購買熱情顯著提升——2015年前后,失眠人群愿意為睡眠產品買單的承受金額大約是幾十元,而到了2018年,這一金額躍升到將近2000元。
聞“眠”而動的創業者
除了以上的消費品,受益于智能設備的普及,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初創公司開始投身睡眠領域的創新,為“睡眠困難戶”們提供更多全新選擇。
“在智能睡眠硬件這個賽道,先是手環教育了一波消費者,接下來2017年CES也教育了一波,2017年CES正式推出了睡眠科技展區,與此同時,巨頭也不斷在入局這個行業,蘋果、諾基亞、三星等都在投資這個賽道。”黃錦鋒告訴億歐。
根據艾瑞咨詢2016年發布的《中國醫療健康智能硬件行業報告》,2013年、2014年運動手環類智能硬件的興起,引發行業內其他產品火熱銷售,2015年智能設備持續升溫,2016年智能硬件市場較前一年增長30%,其中智能睡眠類產品是增速最快的類目之一。
2015年9月,三星發布了睡眠追蹤器 SleepSense;2017年5月,蘋果則收購了芬蘭的睡眠監測器生產商Beddit,將其整合到Apple生態里,例如通過iOS和Apple Watch來控制Beddit睡眠監測器。
不過相比這些巨頭,Sleepace享睡在睡眠市場上的起步要更早一些。
2011年,目睹身邊親人、朋友的實際需求,黃錦鋒成立了一家聚焦睡眠安全的公司,起初推出的兩款產品都沒在市場上泛起水花,直到2014年,公司轉而更加聚焦睡眠健康,憑借2014年11月發布的RestOn智能睡眠監測器,Sleepace享睡這一品牌才在市場打響。
在Sleepace享睡打響名聲的同時,另一名創業者高嵩也看到了非可穿戴設備的潛力。次年,他帶領團隊推出了能夠感應用戶腦電波的智能睡眠枕,以及搭配枕頭關聯使用的蝸牛睡眠App,集呼吸錄音、催眠音樂和睡眠圖譜于一體。
后來,由于硬件堆疊導致的巨額成本以及供應鏈優勢上的缺乏,智能睡眠枕并不為消費者所買單,與此同時,非核心產品蝸牛睡眠APP,卻在沒有任何市場推廣的情況下,用戶量與日俱增,于是,高嵩轉而以軟件為核心,將蝸牛睡眠做成了一個幫助解決睡眠問題的平臺。
根據鄒鄒的觀察,睡眠服務的確有很大的市場需求。在創業做心理類應用軟件“心潮”的過程中,她發現睡眠服務是該軟件里排名前三的需求,與此同時,睡眠問題也是大家比較樂于在社交圈上分享、談論的,“睡眠這件事有很強的社交屬性。”鄒鄒說。
這也是與蝸牛睡眠屬同一賽道的小睡眠創立的由頭。2017年初,趁著微信開放小程序的間隙,鄒鄒帶領團隊推出了“小睡眠”小程序以及APP,基于助眠音樂提供睡眠問題解決方案,目前其C端用戶已經超過9000萬。
小睡眠APP(左)和蝸牛睡眠APP(右)
兩款APP林琳都用過,至今這兩款APP仍然安裝在她的手機上,“之前用蝸牛睡眠監測過睡眠質量,六七十分吧,現在睡不著的時候,也會在上面聽聽雨聲,蝸牛睡眠的夢話監測做得比較好,小睡眠的音頻量比較大”。
睡眠經濟下的冷與熱
作為創業者,鄒鄒與黃錦鋒的感受十分一致:近幾年來,中國消費者對睡眠這一事情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整個睡眠經濟市場也越來越熱鬧,除了初創企業在崛起,傳統公司甚至與睡眠關系不大的公司,也想從中分一杯羹。
鄒鄒就曾碰到過一個“奇怪”的合作需求者,此前,歐姆龍血壓儀找到他們希望開展合作,“我們當時很奇怪,血壓儀跟睡眠能有啥關系”。
后來才發現,高血壓群體99%存在睡眠問題,如果血壓儀能夠附帶上睡眠的服務,不管是在治療過程中還是預后,這些群體的睡眠狀況都有望得到改善,“甚至有些作用還可能是反向達成的,睡眠改善了血壓會不會降下去”,鄒鄒說道。
對于整個市場,黃錦鋒表示,目前市面上針對睡眠干預的公司,基本都是從心理咨詢服務、寢具、睡眠管理、睡眠環境調節等這幾個方面做起來的,但似乎并沒有一個綜合性的巨頭公司,“畢竟睡眠問題還是太復雜了。”
根據博思數據的不完全統計,中國睡眠產業企業數量約2000家,涉及床具、床墊、睡眠紡織品、功能家紡、枕具、健康睡眠系統、改善睡眠保健品、助眠用品、助眠食品、睡眠醫療、睡眠科技研發、睡眠服務等領域。
盡管睡眠市場很大,但由于睡眠問題錯綜復雜,涉及生理、心理諸多因素,因此睡眠相關企業只能散落在各個細分領域,難以形成聚合,也很難出現巨頭或是獨角獸——這是睡眠問題性質導致的市場反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消費者對睡眠產品、睡眠軟硬件滿是熱衷、付費購買的需求也在急劇增長,本以為這個市場會就此按下發展的“快進鍵”,但資本似乎對此有所猶豫。
10月底,號稱“智能電動床第一股”的麒盛科技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掛牌上市,上市首日封漲停,但隨后的兩個交易日均以一字跌停收盤,后續雖有反彈,但仍被視為“最慘新股”。
CVSource投中數據則顯示,近一年內,助眠市場的融資事件及融資金額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睡眠市場的融資事件下降46.71%,然而市場退出事件卻上漲了28.3%。
有投資人指出,目前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在于,市場上不少企業都是在渾水摸魚,推出的產品數量在增多,質量卻不怎么見漲,“產品沒有壁壘,這個市場目前投資意義不大。”
編輯:楊旭然

投資界
4360篇文章TA的動態
2022-07-13 投資界發布了 《粉絲社區服務提供商「花果山傳媒」獲B站投資》的文章
2022-04-20 投資界發布了 《深圳市政府引導基金又要投5家GP》的文章
2022-04-19 投資界發布了 《廣西兩支新基金成立,總規模40億》的文章
2022-04-19 投資界發布了 《石家莊擬設立20億元數字經濟子基金》的文章
2022-04-14 投資界發布了 《西安市創新投資基金首批子基金申報指南正式發布》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