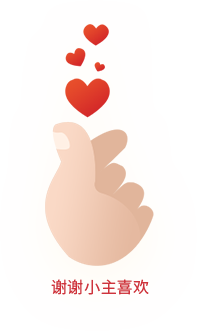二手玫瑰梁龍:哥玩的不是音樂,是藝術
虎嗅注:有個人,他特愛在綜藝節(jié)目里說沒人敢講的大實話,他因為拍攝“辣眼睛”的美妝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刷屏,他還做了不少跟藝術有關的生意,他用實力證明自己的搖滾范兒。他是自稱是“中國搖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二手玫瑰主唱梁龍。以下是8月30日在虎嗅NLive現(xiàn)場,梁龍所分享他眼中的藝術與搖滾。
梁龍(二手玫瑰主唱):大家好!今天給大家分享的是我從2000年到北京做音樂,一直到現(xiàn)在從事一些跟音樂和藝術有關的事,說叫項目吧,但沒有那么準確,但是是一個我們在探索的方式。
現(xiàn)場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我是干嘛的,我是自己做了樂隊,名字叫“二手玫瑰”,因為沒能去“樂隊的夏天”,所以也沒有那么火。
我2000年到北京,那一年就說了一句話“大哥你玩搖滾,玩它有啥用”,這句話惹毛了一批當時北京搖滾老炮,說這個人太不善良了,一來北京就提出了這么一個嚴肅的問題。
實際上二手玫瑰當時看是以一個比較另類的,以色彩的方式來介入音樂圈的。這是我們當年比較有l(wèi)ogo感的一張照片(看圖),當時我是2000年8月份來的北京,正式以二手玫瑰樂隊的名義去演出,那時候我們是用反串的角色,而且唱的方式也比較戲劇化,舞臺表達比較夸張,有的文化人可能會夸我們像個藝術品,但更多的人覺得我們是在嘩眾取寵。
這個搖滾樂不是西方典型的搖滾樂,舞臺也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很硬漢、很風格化的,是一個很怪誕的,看起來很民俗,但又說不清的狀態(tài)。那時候就注定了將來發(fā)生的一些事。
從音樂身份到創(chuàng)作身份
從2000年到北京,我們就一直做著這個樂隊。直到2007年,一個很巧的事打開了我跟藝術窗口的結合。
2000年演出的時候我穿了一雙紅皮鞋,是當時的鼓手花了50塊錢在一家大號女鞋店(因為我的腳比較大44號)買的一雙皮鞋,我一共穿了七八年。
到2007年的時候它就走不動了,因為那一年巡演很多,汗已經把鞋泡的完全碎掉了。我就說“算了吧!把它扔掉吧!換一個新鞋吧!”那一年正好我要去紐約參加一個亞洲藝術博覽會演出,當時有個畫家叫楊旭,他說你應該背著這雙鞋出一趟國,因為這是你第一次去美國,它應該跟你一起去流浪一次,應該去海外。
他說的話,聽起來好像只是一個比較有紀念感覺的東西,但在我心里烙下了一個記憶和記錄的作用。我覺得這個話說的我很感動。后來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他說“我覺得這個紅皮鞋在我們架子上或者繪畫人眼里可能像個藝術品”,當時他還畫了一幅這個紅皮鞋。
然后如他所說,我?guī)е@個紅皮鞋去了美國,演出然后回來。但這事沒完,2007年我又第一次產生了所謂創(chuàng)作沖動,我從音樂身份換到了創(chuàng)作身份。
這個背景就是一個臭水溝,冬天凍上了,有一點點白雪,我就把它放在這個位置,當然還有一些其它的圖片,也放在了不同的位置,我就拍了一組照片,中文“破鞋”,英文叫“l(fā)over”。
我們拍的是黑白的,像很早以前的照片是用手繪的彩色,我專門找了這樣一個老師,用手繪出來了紅色,用刀在照片上刮了一些圖像,是是而非像大腿走動的一些方式和方向,就為了這雙鞋拍了一組作品,也就是在2007年,我從音樂人身份第一次開始跟當代藝術進行了接觸。
二手玫瑰本身有一個氣質,就是他們自認為很民俗化,雖然也有很多人會很討厭我,后來又有這么幾個當代的沖動。我在2008年干了一個更沖動的事情,把我當年兜里的這點錢全揮霍沒了。
2007年我發(fā)起了一件事——“你在紅樓,我在西游”。因為我接觸到了當代藝術,我覺得這個很有趣,但我不知道它跟音樂有什么關系,我突然說想集結幾個音樂人,做同樣一件事,就是翻唱《紅樓夢》和《西游記》的老歌,當時我寫了一個slogan,邀請他們的一句話叫“與其我們展望未來,不如先從閱讀過去開始”。
中國當時的一些當代音樂人,對咱們自己的一些文化其實不是特別了解,那時候大家覺得很無趣,京劇或一些傳統(tǒng)戲曲,確實讓我們感覺有點生澀難懂,那里面有沒有好的呢,肯定是有的。
所以,我就突發(fā)奇想,能不能翻唱《紅樓夢》和《西游記》的經典老歌,讓樂隊來唱。當時我邀請到了后來比較有名的萬曉利,包括當時比較有特色的“雨水門”等,大大小小一共叫了大概10個音樂人,一塊完成了這次致敬的翻唱。
在這個致敬翻唱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好像我這個點打的還挺好,因為當時有個樂隊叫“液氧罐頭”,他給我發(fā)了短信,說我們從來沒想過用重金屬的音色來演繹“葬花吟”這種音樂,沒有想到這種民樂的調和重金屬發(fā)生關系之后產生那樣的分泌,他們感覺很有趣。
我是生生硬硬的把一些藝術品集結進來了,意思就是說,他們每個人翻唱了一首歌,然后我把這個專輯做成了一個畫冊,一片紙是一個藝術品,翻開是歌詞。也就是說,用最硬的手段,把藝術品和音樂做了一個畫冊式的拼接,而且每張作品的來源都不一樣。
在2008年,我又去美國做亞洲藝術博覽會的時候,就把這個畫展搬到了紐約,當時也有很多藝術家朋友支持。我能記住的,比如這幅畫會跟某一個紅樓夢的歌曲做混搭,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把所謂的當代藝術和我認為比較優(yōu)秀的當代音樂做了一次跨界結合,當然結局很簡單,就是賠的一無所有,因為整個展覽過程,包括做畫冊,而且我們沒有辦法銷售,因為那時候有版權問題,我們只自己紀念發(fā)行,沒有辦法正式發(fā)行,所以就是把這個事情完成了,完成之后就把這事基本放下了,該做樂隊做樂隊,該干嘛干嘛,這事好像似乎跟后來的故事也沒關系。
一直到2012年,我即將面臨與簽約公司解約的時候,發(fā)現(xiàn)產生了一個最大的問題: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了,大概有兩三年時間是這種狀態(tài),比如我來北京之前,我認為我是想做一個樂隊,能出一張專輯,能靠你的樂隊去養(yǎng)活你吃飯,好像這就是我在北京的一個終極目標。
突然發(fā)現(xiàn)這點事好像也不是很難,七七八八的也都做成了,那下面做什么?我當時就處于一個真空的狀態(tài),那時候突然把我之前做的紅樓、西游的事想起來了,我想在這里找到一種可能。
當時我給自己的定義是,可能我的個人理想時代結束了,我的公共理想時代開始了。意思就是說,我個人的理想可能是個搖滾樂隊,這個事情可能已經到它該有的宿命和段落了,不是說樂隊不繼續(xù)發(fā)展,而是,它在我的思考范圍里可能已經歸成一條路之一了,下面我要做的可能更多是公共理想。
其實“紅樓、西游”這張合輯已經是半個公共的事情了,光說不練不行,我就成立了一個團隊,當年的名字叫“為搖滾服務”,現(xiàn)在叫ATR。
從群體回到個體
二手玫瑰從公司出來之后,我們要獨立運營,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些音樂圈的故事,作為一個樂隊,一個藝人做獨立運營其實是很辛苦的,因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們所有的宣傳部門等之類的都要具備。這時候我們就做了這個團隊,但團隊只帶動一支樂隊顯然是不合適的,我們就開始試著嘗試找一些音樂與展覽、與美術館、藝術品之間合作的可能性。
我們?yōu)閾u滾服務做的第一個項目叫兩岸三地音樂華人搖滾展,就是我集結了香港、臺灣、大陸(三個地方)在同一個年代發(fā)生的不一樣的搖滾事情。
這是我們2014年,也是成立團隊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我自己開畫廊,有一點便利條件,所以就在我們的畫廊里做,我在北展的這個位置其實還原了一個地下室,可能現(xiàn)在好多朋友都不知道地下室的概念,就是我們那個年代來北京基本上都是睡在地下室。有錢的睡地下一層,沒有錢的睡地下二層。關燈就是黑天,開燈就是白天,你所每天對抗的就是老鼠,因為它會吃掉你買的烙餅。
這個記憶其實對于我們那一代的北漂是非常深刻的,我記得我站這個位置擺了一張床,那個床就是還原了當時地下室的一個狀態(tài)。我去了幾個老朋友,大概都是像我這種70后,就是有點中年油膩的男人,去的時候看到床,眼淚就下來了。有幾個老樂手,一下回到了他們那個年代,這是我們做的第一件事。
到了2015年,我發(fā)現(xiàn)展覽是一種文化的體現(xiàn),但它不是一個活動,活動的范圍非常窄。展覽只能傳遞信號,那我們什么時候才能去動手呢?2015年我們做了第二件事情,叫做搖滾運動會。
搖滾運動會是一個演出為載體的一個活動,就是最早簡單點說,我們想集結幾十支樂隊,像擊鼓傳花一樣,從東北比如說二手玫瑰是東北來的樂隊,我們做第一棒。然后演到北京,比如找一支北京的音樂人傳接第二棒,再到內蒙接第三棒,再到西北接第四棒,我們想做這樣一個傳接式的音樂巡演。
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每一個音樂人都是本土音樂人,你必須得發(fā)現(xiàn)或發(fā)掘一個新人,或者是之前在這個土地上非常有名的音樂人,但現(xiàn)在后來不做了,我們要把他發(fā)掘出來。但由于我們當時的能力不足,只把這個巡演大概做了一半,真正想挖掘土壤里的音樂內涵的東西,其實我們沒有做的那么好,2015年,我們就做了一個搖滾運動會。
其實我們最后的理想,是做一個真正的運動會現(xiàn)場,可能像一個音樂節(jié)一樣,把這些藝人都找來,比如說謝天笑撇鉛球,高虎撇標槍,看誰跑的快,最后一看搖滾圈全病秧子,沒一個能跑起來的。
想做那么一個事,但是這個其實沒有達到我們那么好的效果。當時我發(fā)現(xiàn)我們只有思考的,就是我們動手能力沒有那么強。所以接下來我還是得去思考,這個團隊到底要找什么,到底要在這個文化系統(tǒng)里面推進什么、做什么,一直是在一個思考的路上。
這個過程其實我們還是挺幸運的,因為那個年代我們還真是拉了一點贊助,說白了有人投錢,所以我才能請了這一票人去參加我們這個活動。當時那個年代其實像痛仰、馬條、郝云,這一幫人都已經挺貴了,都得給錢了,要不然走不動道了,都十萬二十萬了。
然后找了這些朋友來支持,我們也做了一整套的美學系統(tǒng)。我覺得這次巡演雖然沒有達到我們那么好的效果,但是在整個的美學出品和我們想要的東西上,已經慢慢接近了我那個夢想里的東西。雖然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我感覺接近了。
那么知道搖滾運動會做完第一季之后,反正莊家第二季也不投了,我們發(fā)現(xiàn)帶動一群人去解讀一個問題很吃力,接下來干嘛呢?接下來我們干一件事,就是既然我解釋一群人好像解釋不清楚,我先解釋自己,我又從群體回到了個體。
在2016年,我做了一個個人化的行為,就是只把二手玫瑰一支樂隊解剖。
怎么解剖?我們做了一個叫允許部分藝術家富起來的多媒介交互戰(zhàn),這是二手玫瑰單元,就是把二手玫瑰樂隊分為幾個部分來體現(xiàn)出來。我想讓很多音樂人和藝術家看到,那么有一點所謂質感的音樂,它如何和藝術、和市場、和美術館發(fā)生關系。
這是展覽的一部分,其實內容涵蓋挺多的。
這個(上圖)是當年的工人體育館,搖滾無用演唱會藝術家做的衣服。這個門是一個藝術品,包括那兩頭豬,是根據(jù)我們歌詞做的一個當代的裝置,包括我們這種多媒體做了一個“紗 | 界”交互的MV影像。包括豬飛上天,這個底下紅魚缸是我個人的作品,是一個東北稻花布包裝的一個紅魚缸。我們等于是從四到五個層面去解剖一個樂隊,解剖一首歌。
另外一個墻其實特別震撼,是把我這首歌的24句歌詞,每一句歌詞都用一個藝術家的藝術品來代表,那一面墻一共放了24個藝術作品,是解讀一首歌。然后這個策展人是鄭路,我的好朋友,他說希望不光我給藝術家提出一個問題,他們按我這每一句話去做每一個藝術品,可能這些藝術家也會回饋給我一句話,我再變成一首歌。
我突然發(fā)現(xiàn)這個感覺有意思了,就是在音樂給了樂隊自己一個復合解讀的能力之外,我們開始和當代藝術真正近距離的發(fā)生關系了。我做完這個展覽的時候,請了一些音樂人朋友到現(xiàn)場,他們都非常驚訝,他們跟我當時說:“梁龍,我大概知道你要什么了”。這種感覺好像慢慢越來越明朗了,但我們其實沒有找到最后的答案。
直到2017年或者是2018年,我就編了四個大字,叫做藝術唱片,這就是今天講的真正的核心主題的東西。
音樂:公共性很強,當代性不夠
先說一下它的由來。我是有一年去臺灣參加一個藝術博覽會,看到了一幅板畫,這個板畫是帶著一點多媒體效果的。它有一個燈在慢慢的循環(huán),像一個門,這面像一扇窗,外面像風景。
我就站在那個板畫的前面,駐足了幾分鐘,因為它吸引我了。我突然腦子里閃現(xiàn)出一首歌,張楚的《愛情》。我就感覺這幅板畫如果能唱一首歌,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是我喜歡的藝術品,然后里面又有一首我喜歡的很牛逼的作品,我覺得這兩個結合可能更好玩。
說白了,第一次發(fā)現(xiàn)如果藝術品能唱歌,是挺牛掰的一件事。回來之后我就給自己起了個名叫“藝術唱片”。一開始的想法也沒有那么夸張,我就希望好的當代藝術品和好的當代音樂能做一個貫穿式的結合。那么這兩個在一起的話,能不能產生更多的分泌?
我不知道現(xiàn)場的朋友有多少是接觸過美術或者音樂圈的,我去中央美院,前兩年偶爾打籃球,他們認識我的人并不多,但是能把我當成當代藝術家的特別多,(我)禿頭嘛。但是我有好多藝術圈的朋友,我們茶余飯后聊天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美院保守地說,有50%以上的當代藝術家、青年藝術家,他們對獨立音樂、對原創(chuàng)音樂非常感興趣。
簡單說吧,他們很多人在聽搖滾樂畫畫。然后在音樂節(jié)現(xiàn)場,你會發(fā)現(xiàn)去音樂節(jié)的年輕人,對顏色和結構特別敏感。我就感覺這兩個群體的黏合度特別高,所以覺得我做藝術和唱片這兩件事,應該能找到出口。
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就開始求爺爺告奶奶,做了第一個展覽。第一個展覽我是給謝天笑打了一個電話,我說我要做一個藝術唱片。他就一臉懵逼,他說什么叫藝術唱片?我說這樣,你選擇你一首歌,或者你一張專輯,你認為它是想做藝術唱片這種概念的,然后我來負責找一個藝術家,跟你做一個結合。
他就選了一首歌叫《永遠是個秘密》,我當時記得好像是。后來找到我的朋友鄭路,那么我們就做了第一屆在什么都摸不著門的情況下,做了第一個藝術唱片的展覽叫《嘮嗑》,因為選的是《永遠是個秘密》,也叫《秘密之約》。
這個藝術家在我的畫廊把整個一面墻包成了一個房間,整個橫向包了一個房間。在房間的里邊,這個墻的后面,我們一共用20臺電視,這個電視里播的是謝天笑的一些采訪,還有演出的花絮。
然后整個這面墻是用什么做的呢?大大小小的凸透鏡,在這邊你可以看的更清楚一點。當你看到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好像里面似乎有內容,所有的觀眾就會貼近去看。但其實誰也看不清里面具體的內容表達,然后再循環(huán)播放著《永遠是秘密》那首歌,但是重新做了一個remix版。就是又有點跑調,又沒有點跑調,我們整個定義為《秘密之約》。
然后墻的兩側,從那個點大家可以看出來,可能有點不明顯,我們貼了一圈盲文,也都是用點來代替的,其實那就是歌詞。
當然了,這是第一次實驗,而且整個的感覺稍微有點生澀,因為藝術有時候確實有點難理解。這次來特別搞笑的一件事,謝天笑的歌迷來了以后全部坐在墻后面等著,誰也不往前去。我在下面說你們?yōu)槭裁床煌叭ッ幻⒖匆豢础⒙犚宦牐克麄冋f當代藝術搞不懂,就是我發(fā)現(xiàn)有點太高冷了。我頭疼,我說不行,第二屆我要換個方式。
第二屆我們就稍微熱鬧一點了,色彩派對,當時我請到的是藝術界的網紅,叫趙曉佳。可能有些人知道江湖有個劈叉哥,一劈成名,這也是個畫畫的叫趙曉佳。后來我找的李志,我說你們倆做個結合吧,道理如出一轍。
我發(fā)現(xiàn)音樂人在藝術家面前變得特別羞澀、保守,我說我拉個親吧,李志說別拉群,他說你就跟他交流吧,他說我就不說話了。然后我就跟這個藝術家說,我說那趙曉佳老師,怎么去跟他做結合?他說沒問題,他說我給你選擇一個熱鬧的方式。
他用了一個叫現(xiàn)場作畫,那天展覽的現(xiàn)場,李志到現(xiàn)場之后他只畫開了第一筆,就是比如他畫了一個M,或者畫了一個W,他就可以休息了。剩下的整個繪畫過程,是由這個藝術家現(xiàn)場完成,然后一直放著那首歌,一直去畫。
大概用了我印象里可能是2個多小時吧,這次展覽比第一次能好一點了,什么呢?就是大家能動起來了,就是這幫人看畫挺逗,但是這個藝術家也挺舍得開的,一通潑墨,然后這幫人就等著看最后能畫成個啥。
這次要比第一次好,但是我發(fā)現(xiàn)還是一個問題,依舊沒有脫離這個,我沒有到一個互動性,還是那么沒有互動性,沒有那么好。
然后第三個我就開始思考了,這是最后作品完成,但是這幅畫出了一件事,也把我嚇一跳。這哥們兒畫挺貴的,有一次我在外面辦事,畫廊的小姑娘說出事了,我說怎么了?因為這個藝術家玩了一票,就是把這個畫畫的筆沒有去收,他說展覽就全放到那兒沒事,來了一個女的可能也挺藝術的,她就以為這個是沒完成的花,她覺得自己有義務把它接著畫完。就亂套了,她直接在旁邊一通比劃,就畫了一堆別的東西,然后我就傻了,我就懵圈了,這個女孩也跑了。
正常來講這個藝術家他要說50萬我就得賠50萬,他要說80萬我就得賠80萬。然后我也冒汗了,我說這麻煩了,就是哥們兒打個半折也幾十萬,后來趙曉佳來到現(xiàn)場看了一眼,說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我的她最后這幾筆完成的還可以,當時我心就踏實了,還好碰到比較開朗的藝術家。
那么這兩件做完之后,我說了互動性不夠好,第三次繼續(xù)去做實驗,我找到了郝云。找到郝云的時候就麻煩了,雖然我跟郝云私交很熟,但是他比前兩個更難對話,為什么?郝云感覺自己的作品可能沒有那么地所謂的“藝術范兒”,他說,我這個說白了是民謠也行,搖滾也行,但這個東西能不能達到你的效果我不敢保證。
我們倆就從酒吧,從9點多一直喝到凌晨3點,我實在喝不動了,我最后就跟他說了一句話,我說你就信我的,但那句話后來也變成我一個slogan,我說好的音樂是可以進美術館的。就是這一句話,他似乎就明白了,好的音樂可以進美術館,他說那我答應你。
然后我們就用一個比較有互動性的方式,其實大家現(xiàn)在比較臭大街的就是那個網紅展,就是運用了多媒體。我們整個就是把這個畫廊三面全打成了鏡子,然后整了幾臺投影儀,然后開始嘗試用多媒體帶一定的交互技術來完成這首歌,當時我們選擇的是《四季不敗》。
當時那個年代比較簡陋了,就是這個感應器,星星點點的,你一碰到它,它就跟著你的速度走。你說停,它就停。大概有這么一點互動方式,黏合度明顯高于前兩個。就是這里邊會看到男男女女不走,他會看好幾遍這個展覽,因為有好幾個角度。
我發(fā)現(xiàn)多媒體好像在藝術與音樂之間的介入會有一定的幫助,所以我在下一個展覽的時候,就另一種方式去做。
當然我首先說第四個展覽我邀請了鳳凰傳奇,這時候好多藝術家就不太高興了,說梁龍你做的不是藝術唱片嗎?你為什么找鳳凰傳奇?我說鳳凰傳奇很藝術、很傳奇。
我覺得鳳凰傳奇特別傳奇,我就給鳳凰傳奇的老板打電話,我說能不能參加這個展覽,老板比藝術家想的非常開通,他說梁龍你折騰吧,我看你怎么讓我藝術,就這個意思。
然后我這次就沒有選擇一對一的藝術家和他合作,我選擇了一個招聘制。我把前三期做了一個推送,我說這就是我想要的一些東西和方向,那么誠招廣泛的社會上的藝術家,誰有興趣可以報名,這次采取了一個報名展,一共大概有四位還是五位藝術家參加這個展覽,四位。
這次就是比較立體了,你看這個有裝置類的,像鳳凰這樣的,這兩個是裝置,然后有架上藝術,然后這個是我要重點說的,你看這只有六面鏡子,這是六面鏡子。這個時候有一個人給我發(fā)了一個郵件,這個人說你這個項目我觀察了一段時間了,他說我不是藝術家,但是我認為我有可能會跟你去聊這個事,這個人叫倪曉光,現(xiàn)在在上海。
我說你是做什么的?他說我是做編程的。然后他就給我講了一下他認為的將來音樂現(xiàn)場互動的一些方法和形式,特別打動我,我說你直接買張機票來北京吧,因為他當時在大連,他第二天就買張機票來北京了,然后我們倆直接見面就聊了。
他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路,他說:“你能把鳳凰傳奇的那個分軌文件要來嗎?”我說你要做什么呢?他說我可以把這個分軌文件定幾個點,其實這種科技技術不是很復雜,我只是說創(chuàng)意。他說比如說我們做完之后是這樣,因為我是給他做了一個藝術現(xiàn)場,他的這個柱子會打了六條類似于分軌的信號。
然后站在第一個鏡子前面的時候就是“留下來”那句話,第二個就是“動次動次動次”,第三個就是“蒼茫的天涯是我的愛”,也就是說你六面鏡子都站上人,一起蹦才能播一個完整的那首歌。
當時也是因為這場是第四季,是當年的收關之展,我就邀請了很多音樂范圍的朋友來現(xiàn)場,看到這個時候什么馬條他們說,老梁我明白你要做什么了,可能你做這個東西和將來的舞臺包括音樂進展覽館(有關系),有點打開我的思路了。比如說鳳凰傳奇可以在你專場的現(xiàn)場做一個裝置出現(xiàn),這個鏡子可以作為跟歌迷或者成員互動交互的呈現(xiàn)等等。
慢慢他們就覺得好像藝術唱片這個東西越來越明朗了,但其實對于我個人來講是越來越模糊了,因為做了四個展覽之后,對于我來講依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tǒng)化的可能,我不知道如何形成一個把更多的音樂人和藝術家能很容易的在一塊交流這件事情,所以對我來講還是沒有找到答案。
雖然我的產品答案沒有想到,但是我對于這件事堅持做下去的理由我找到了,這就是那六面鏡子。
我做完這個展覽之后,我總結的就是我在做什么。因為這個音樂的當代性很差,什么意思?就是我們現(xiàn)在的這個環(huán)境,對一些所謂的藝術化的音樂沒有一個定義。比如說我認為莫西子詩的音樂是藝術品,那么在我們真正的市場里,也只能把它歸納為好聽的小眾音樂。對于我來講這是不夠的,我講一個故事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前些年我去德國演出,看了一個德國戰(zhàn)車的MV,特別暴露,我想這國內買不著,我在那兒買一張回家留個紀念什么的。結果我到音響店買的時候,在搖滾欄從頭扒拉到尾,沒買著,我說不可能,這是國寶級樂隊,怎么可能在這個國家沒有德國戰(zhàn)車呢?我就問服務員,最后服務員跟我說,德國戰(zhàn)車的CD在古典欄里放著。他們對音樂的認可,是當年很刺激我的一件事情。
音樂的當代性,目前在我們國內范圍是非常差的,沒有一個博物館、美術館類的音樂,比如說音樂博物館,我們沒有這樣的地方,我們沒有把好的音樂給到他一個好的當代的位置和文化背書,這是我對音樂不當代的一個心結。
那么它的優(yōu)點是什么呢?音樂的公共性很強,因為只要你一張嘴、一演出就是給大家唱的,你一上網絡就是給大家看的。也就是說中國一個一流的一線門戶藝術家,也沒有一個三流的喊麥粉絲多,就是說音樂的公共性很強,要比藝術。
那么反過來,藝術的當代性很強。說是搞藝術的,當代藝術作品,但是藝術的公共性很差。我們能看到目前走入生活的,無非就是超貴的商場,或者是五星級賓館,其實那個我不認為它真正的走進了公共,它還是在一個特定的位置去給一些特定的人群去展現(xiàn),或者說它的公共性還沒有真正和生活發(fā)生關系。
通過這兩個點,我發(fā)現(xiàn)音樂當代性不夠,公共性很強,而藝術當代性很強,公共性不夠,最后我就總結了這么一個對于藝術唱片基本的解答。我希望的是,音樂通過藝術走進當代,藝術通過音樂走進公共。能不能實現(xiàn)這么一個價值的可能性?但也一直在摸索,現(xiàn)在可以預先播報一下,目前我們將在10月31日,在北京舉辦一個新型的藝術博覽會上,藝術唱片將舉辦第五屆。
第五屆也就是我們要給市場一個答案,可能這個答案是要能通用化的,讓更多的音樂人和藝術家能一塊兒進到這個范圍里去玩,去一塊兒參與。但是效果能不能那么好,現(xiàn)在我也不敢做預期。
今天其實我講這個是一個沒有結果的主題,就是希望大家能有更多有智慧的人,不管是音樂從業(yè)者,還是藝術從業(yè)者,都能一塊兒去群策群力,能把我們的中國好的音樂,把它像美術館一樣的標簽化,能讓好的藝術作品,通過公共手段推到更多的大眾領域。
下載虎嗅APP,第一時間獲取深度獨到的商業(yè)科技資訊,連接更多創(chuàng)新人群與線下活動